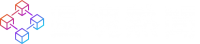這不是民衆第一次希望代碼成爲「法律」,儘管「法律」在具體語境裏更像「不可侵犯之神聖準則」。
1787 年,美國聯邦憲法正式頒佈。儘管這套海洋法系在當時看起來無比先進,但知識分子、法學家們對它的批判從未停止。
20 世紀下半葉,這種不滿變得劍拔弩張:光否定美國政法體系早已不解渴,批判者將矛頭直指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市場經濟。他們高呼「市場威脅了自由」。
1990 年的聖誕節假期,籍籍無名的網絡工程師蒂姆·伯納斯·李,利用閒暇時間創造了現代互聯網的前身——萬維網。伯納斯·李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寫下了舉世聞名的概念「去中心化」並深得知識界的歡心。「網絡天生能夠抵禦幾乎所有形式的控制」、「(網絡)使法律陷入混亂」、「代碼即法律」……目不暇接的報告振奮人心。
直到現實打了所有人的臉。現在,微信成了連超鏈接都不允許存在的超級應用,管理全球十分之一以上人口的生活。
理想主義者也必須承認一個現實:虛擬世界不是遺世獨立的,它不僅受到了控制,其本身也已墮落成控制的工具。
不知死,焉知生。我們需要互聯網的經驗。這並非用舊事物強行解釋新事物,因爲有些東西從未改變(善?),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改變(善?)。你無法忽視它們。
所以這種質問是合理的:當區塊鏈重拾「代碼即法律」的古老信仰時,是否踏進了某些拙劣且重複的陷阱?區塊鏈和互聯網的不同是什麼?超前之處又在哪裏?
溯本清源
區塊鏈行業主流語境中的「代碼即法律」,並非嚴謹的學術或商業概念,而是一種原教旨主義式的技術信仰。
不久前,EOS 上頻繁爆發的黑客襲擊貢獻了久違的行業熱點。那場討論中,最「原教旨主義」的觀點來自區塊鏈程序員羣體——
從代碼這一「規則」角度,黑客的攻擊,也可以視作合約所允許的一種「玩法」,黑客精妙地發掘了「裏メニュー(隱藏菜單)」,並贏得了「獎勵」……基於客觀規則的行爲,如果因此受到懲罰,那麼無疑會助長更多對規則的破壞和不公正的行爲。
簡單翻譯一下:爲了維護代碼作爲法律之神聖不可侵犯性,基於代碼——哪怕是利用代碼漏洞——的任何行爲都具有正當性,不應遭受制裁。這也是目前「代碼即法律」最流行的詮釋。
與其稱之爲法律,倒不如直接翻譯成《聖經》。任何「異教徒」都應施以車輪之刑,豈不快哉?

這種想法可不是什麼新鮮事。
「代碼決定一切且毫無疑問擁有這種能力」的觀點肇始於伯納斯·李的萬維網。「網絡天然擁有抵禦一切規制的能力」也是美國學界定義網絡空間的最初理論。
迷幻搖滾樂隊「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詞作者的作品《網絡空間獨立宣言》代表了當時無比樂觀的輿論情緒:
工業世界的政府們!你們這羣令人厭惡的鐵血巨人!我來自網絡空間,思想的新家園。我代表未來,要求落伍的你們離我們遠點兒!在我們聚集的地方,你不再享有主權。
可是也有異論。
美國憲法學者、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在 2004 年出版的《代碼:塑造網絡空間的法律》一書中,將代碼作爲現實中法律的映射來研究。
儘管二者存在巨大的不同,但從蛛絲馬跡中萊斯格悲觀的發現:代碼如同服務於民主政治制度的美國法律一樣軟弱,它甚至不具有中立性,網絡空間擁有什麼樣的性質,完全取決於代碼架構由誰設計、如何設計。
互聯網的性質並非上帝決定,僅僅是由它的設計架構決定。
這是條不可抗的「客觀規律」,在網絡降生的那一刻就已隨之而來。
在萬維網出現之前,互聯網的雛形已經誕生在美國的大學裏,在還沒有超文本鏈接的時代,它只能供大學間傳遞資料用。
在芝加哥大學,如果你想接入互聯網,僅需將你的機器與遍佈學校的以太網端口連接即可,即接入網絡是完全、匿名和免費的。
這一決定來自於一名行政主管、法學家傑弗裏·斯通——著名的言論自由主義者。當技術人員詢問他,是否允許匿名訪問時,他援引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條款。這一政策決定了芝加哥大學網絡空間的狀態。
而在哈佛大學,事情恰恰相反。你想上網,必須得到校方的註冊許可和驗證,個人的機器也將被系統識別確定。在這裏匿名言論不被允許,它與代碼架構不符。這一決定同樣來自於某位領導。
這兩件事實進一步說明:代碼不僅擁有法律效力,並且在封閉條件下擁有私法性質。代碼受到了比現實法律更多的制約,制約來自四面八方——社會準則、道德約束、與之相關的現實法律和政治制度。

代碼無法獨自決定一切,它甚至不具備任何天然的權力。你不能提出以「代碼即聖經」爲前提的要求,因爲它必然是野蠻的。
事實在區塊鏈領域依然如此。因爲,許多能夠制約區塊鏈的內外因素都沒有改變。
「東西海岸代碼」的魔咒
IT 界人士習慣用一些新鮮詞彙來顯示「我和其他人不一樣」,在有足夠影響力的情況下,也不介意再造一些新詞出來。
當法學家紛紛以法律形容「代碼」時,硅谷精英們則用「西海岸代碼和東海岸代碼」來代指科技互聯網與傳統世界(東海岸指華盛頓)的規則。
一方面,這表示我們完全不同,未來與現在、先進與腐朽站在對立面;另一方面,硅谷企圖昭告天下:我們有實力抗衡傳統世界墮落的侵襲。
我們的確看到了硅谷以及它全球追隨者們的實力。
Facebook 接管了世界 15 億人口每天看什麼新聞、或者什麼內容「更好」的控制工作。
過去,希特勒還需要建立層層宣傳部門監管幾百萬人在聊什麼。現在,幾千工程師就能控制一切。
而且小扎不需向任何人負責——他一個人擁有 Facebook 壓倒性的投票權,沒有哪個股東能夠挑戰他的權力。你很難判斷,被三權分立掣肘的特朗普和放飛自我的扎克伯格,究竟誰的權力更大些。

當你把扎克伯格換成馬化騰、Facebook 換成阿里巴巴時,我想結論並無不同。
你會聽到「技術是中立」的辯解,但在越來越集權的信息傳播格局面前,這就像一句笑話。
現實令人沮喪,西海岸最終沒有實現它的承諾:創造出站在華盛頓對面的未來。
首先,造成如今這種格局的是代碼本身的侷限。
代碼的確和法律不一樣,後者發揮效能分爲兩步,立法和司法。在任何政治制度的現代國家中,立法和司法必須獨立。
理由很簡單:法官不能像足球裁判那樣滿場跑,滿場跑的裁判難以處於中立位置,不中立就容易做出錯誤判斷,這也是足球裁判經常捱揍的重要原因。
排球裁判不一樣,他站在場地之外、立於正中間並高於球網,球員觸網或過網擊球時自己都難以察覺,居中裁判者卻明察秋毫。
可是,網絡應用(代碼架構)的設計者卻兼任了立法和司法角色,他們不僅規定代碼如何運行,且代碼直接執行製作者的意圖。
7 月底,區塊鏈遊戲 EOS 狼人發表聲明稱遭遇黑客攻擊。聲明稱,項目被非法盜取 6 萬餘 EOS,並建議遊戲中獎者通過 EOS 核心仲裁法庭申請仲裁。該事件一直被外界認爲是狼人殺團隊監守自盜的行爲。
有一個經典邏輯問題:當你無法論證一個事件不可能發生,同時它還沒有發生,那麼它很可能就在前面等着你。
EOS 狼人事件的猜想就屬於這個問題,區塊鏈代碼完全有可能被用於監守自盜的行爲。現在,你是否還能理直氣壯的高呼「代碼即聖經」?

有個很有意思的題外話,EOS 平臺上的衆多博彩遊戲開發者們,通常選擇不開源代碼。可諷刺的是,賭徒們最初之所以傾心區塊鏈,大抵因爲代碼開源可以防止莊家舞弊徇私,在規則透明的情況下是否賺錢,你我各憑手藝。
然而不開源的博彩遊戲與中心化時代別無二致,任何人無法爲任何項目擔保它一定沒有問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代碼並非遺世而獨立,虛擬空間存在外部效應,影響現實的同時被現實制約。「西海岸代碼」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在向東海岸學習、靠近和妥協。
的確,資本和公權力很難直接干涉虛擬世界的行爲,但卻有一萬個法子去影響虛擬世界的規則。美國政府和資本不需要直接限制所有網絡行爲,他只需要限制網絡行爲發聲的平臺即可。
隨着代碼編寫的日趨商務化——即編寫權力逐漸落入幾家少數大公司的手上——公權力和資本控制代碼的能力隨之增強了。有一個無法改變、固定不變的控制客體是實現控制的絕佳前提。
那些抵抗控制的堡壘,搖身一變就成了強化控制的兵工廠。
1998 年,全球最大的網絡信息安全管理商思科公司發佈了一款路由器,使用者可以在鏈路層加密網關之間的通信數據,不過路由器還有一個開關,可以關閉加密並蒐集所有非加密期的數據。而美國政府可以操控這個開關。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公司膽敢開發違反國家意志的工具,美國政府對其有強大且合法的威懾力。它需要做的,是讓任何一個違背其意願的代價大於違背其他任何意願的代價。
我想在可預見的未來,區塊鏈面臨的主客觀條件也不會有改變。而且,最近已經爆出耐人尋味的新聞了。
希望:強制性放源代碼
態度悲觀不代表毫無希望。
區塊鏈沒有它的擁躉想象中那麼「反互聯網」,只是一脈相承罷了,不僅在技術上師承,在意識形態、哲學思想上也形影相弔。
希望恰恰來自這裏。
20 世紀 80 年代,軟件開始走向商業化。但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理查德·斯托曼認爲這違反了網絡精神,軟件應該讓人們自由地使用和修改,於是他辭去了工作,並創造出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
著名的操作系統 Linux,就是運行在這個許可證上的。現在,我們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超級計算機等,大都給予 Linux 操作系統。
理查德極具黑客精神的行爲獲得越來越多極客的響應,並引發一場持續至今的社會運動——「開源計劃」或稱「自由軟件運動」——爲爭取開源一切而奮鬥。當然,我們都知道他們沒有直接取得理想的結果。
可技術內在要求開源的區塊鏈,就是這一思潮的結晶體(區塊鏈前面還有 P2P 技術,不再贅述),而開源的意義遠比你想象中重大。
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控制加密路由器,是因爲當控制對象思科表示順從時,一般用戶就無能爲力了。可如果一個代碼架構被開源了,事情會不會不一樣呢?
必然會。
1996 年,美國網景公司爲保證電子商務的安全,曾發佈過一組協議(SSL v3.0)。它可以保障瀏覽器和服務器之間數據交換的封閉性,但法國政府很不開心,它希望破譯 SSL 以獲取交易內容,故而對網景公司提出「開後門」的要求。
網景當即表示「臣妾做不到」,因爲它已經公佈了 SSL 所有標準。它當然可以更新一個 SSL 模塊幫法國政府監聽,但任何人都可以開發新的 SSL 代替法國政府的那個。各個模塊相互競爭,得人心者勝出,而大多數人會選擇一個沒有被監聽的模塊。
這個例子很簡單,但意義重大。當代碼是開放、可被修改的,就沒有外部力量能夠保持客體是它所希望的那樣,一個會變來變去的客體不是好的控制對象。
設想你是一個前蘇聯的宣傳人員,你要求每一本書都必須有一章節專門講述斯大林的政績。但這樣的書能夠影響人們的實際閱讀嗎?

書就是開放源代碼軟件,文字對任何內容毫無隱藏,文字暴露了源代碼,文字即源代碼。讀者永遠選擇他們喜歡的章節去閱讀,技術原因賦予讀者不讀斯大林那章的權力,而你對此無計可施。
開源代碼意味着開放的控制——那裏有控制,但已被用戶知曉。
「代碼即法律」不是神話。當人們能夠理性的面對它背後的真實含義,或許,商業力量尚有一絲希望去擺脫「東海岸代碼」的影響。
但這有個前提,商業力量不會決絕地成爲這條道路上的最大阻力。
商業會威脅自由嗎?好吧,這是另外一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