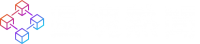吳軍在他的獲獎圖書《文明之光》中說,人總是要有些理想和信仰。當別人問起吳軍的理想時,吳軍就給他們講貝多芬的故事。
一般人看來,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和他的身份並不相符。作爲 Google 中日韓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設計者、原騰訊副總裁、硅谷風險投資機構豐元資本創始人,吳軍這種跨界之爲,讓正在失去集體記憶,依靠手機維持現實暫時性遺忘的人們頗感驚奇。
按照約定,吳軍 13:30 準時走出電梯,如果不是瘦瘦的高個特別精神,他素色襯衣套上棗紅色毛衣這種硅谷工程師的常規裝束,很容易淹沒在人羣中。
稿件來源: 南風窗(ID:SouthReviews)
作者:何子維;編輯:李少威
藝術 VS 技術
「你最近在讀什麼書?」一本深藍色的書引起了我的注意。
吳軍從牀上拿起書回到桌前:「美國人邁克斯·泰格馬克寫的《生命 3.0》。作者從知識性來講人工智能,是一本不錯的書。」
吳軍的書桌上還有一本有關計算機的英文書,這本 A4 大小的書像一本百科全書,應該不下 2000 頁。這是他的本行,厚得有道理。
讀書是吳軍生活的一部分。近期吳軍手裏有從亞馬遜上買的紙質書,有從美國圖書館借的音頻書,還有出版社爲請他作序而寄給他的書。
能夠搶先閱讀,顯然令吳軍滿意。「那些書在 PDF 版的時候,我就已經讀了。出版社常跟我說,你用一個最通俗的語言來寫寫這個基因是怎麼回事吧。」顯然,出版社認定凡帶着理科屬性的書籍都可以找吳軍作序,並且承認,他的每一次跨界都玩兒得很溜。
就像我們承認吳軍是這個時代裏珍貴的互聯網工程師一樣。我們也承認,除了我們還認爲他是跨界達人之外,我們對他其實一直所知不多。

21 世紀的開頭幾年是 Google 的重要階段。
2002 年,拿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的吳軍,放棄了進入 AT&T 和 IBM 這樣的大公司的機會,選擇了與自己的專業有些出入的 Google。
2003 年,吳軍和兩個同事成立了 Google 中日韓文搜索部門,開始了他強悍的事業——他寫的代碼一度佔 Google 整個代碼庫的 0.7%——對於絕大部分 Google 工程師來說,這是個難以超越的數字。由此,位於加利福尼亞山景路,那個稱爲世界上最快最龐大的信息系統,向使用中文的人們敞開了。
作爲搜索之王,Google 的那塊用來顯示全世界搜索的關鍵詞的大屏幕,既是一個時代的記憶,也象徵着年輕的吳軍人生的某個起點。這個在我們看來很重要的起點,吳軍的回答卻很輕鬆:感覺自己能做,便去了。
這是一個帶有理想主義氣息的答案。Google 搜索老大阿密特·辛格哈爾曾經告訴吳軍,「我們的算法都應該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每一個程序在全世界都有上億的人在用,我們在創造、在改變世界。」

《紐約時報》2004 年調查報道稱,谷歌的成功依靠一個神祕的軍團——博士組軍團。在其他公司由一個本科生做的工作,在谷歌則用一個碩士或者博士做。吳軍很欣賞這種方法,稱爲「殺雞用牛刀」。在吳軍看來,這是思維的不同,不是學位的距離。因爲碩士能把你領到別人到過的地方,而博士可以把你帶到以前無人去過的地方。
要抵達前人未至之地,必經一條細節嚴苛和想象深邃之路。Google 的嚴苛給吳軍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爲了界面的簡潔,如果一個程序多寫了一個空格,或者一行超過了 80 字,在 Google 都不允許提交。即便是給程序的變量取個名字,要通過評審,往往也得千迴百轉。
數字、字母、符號堆積的單調和枯燥,遠遠不是《黑客帝國》中矩陣的綠色代碼瀑布那般詩情畫意。編程就是創始,人類就是程序,生命只是意念,令人不安。但吳軍潛意識要把編程變得有如瀑布般詩情畫意。
「每天上下班一小時,差不多聽完一張古典音樂 CD。」談到這段經歷,吳軍其實是心懷感激的。「莫扎特是個很窮的藝術家。他一生都很平靜地寫快樂的曲子,這是件難得的事。人窮了一輩子,但是他的音樂裏從來沒有憂傷。」
莫扎特、貝多芬、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阿圖爾·魯賓斯坦在吳軍的耳朵裏構成了一種安撫。這種安撫帶來的影響是關鍵性的。當華美的樂章在耳畔響起,讓他想象力充沛,讓他能夠摒棄干擾,進入到那個壯闊的綠色代碼瀑布。
技術要與藝術結合的觀念有力地影響了吳軍,還有 Google。在讓艱澀的技術遠離孤島這件事上,Google 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定期邀請作家到公司內部來開茶話會、辦講座,包括因《世界是平的》而紅遍全世界的托馬斯·弗裏德曼。
「早點去,佔一個好座就可以免費得到一本書。」多年以後,吳軍仍然津津樂道,在講座結束後,他還會和工程師們排隊等待作家簽名。
與追星的工程師不同,Google 更想要的是,如何讓代碼與藝術相遇之後起化學反應,使其變得更加柔軟,如何在一個網站內部就實現多元化的信息自給自足,如何創造一種有別於其他互聯網公司的信息文明制度。
Google 這種瘋瘋癲癲的行爲藝術與吳軍有某種契合。只是當初的吳軍還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其實是一場藝術對技術的突圍表演。

吳軍「來信」
作爲早期美國 Google 的員工和後期中國 Google 的骨幹,吳軍很快變得名噪天下。而在國內,三分天下有其一,想把搜索與社交整合到一起做網絡搜索的騰訊,也開始對吳軍出手。
2010 年,吳軍就任騰訊副總裁。按照騰訊的想法,吳軍要做一個類似於百度的搜索網站 SOSO。但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幾乎不知道有 SOSO。看來,這一次命運女神忘記了垂青吳軍。有評論說,吳軍是極好的工程師,但卻不是領軍產品開發的將軍。吳軍也不避諱,他說,騰訊的基因是社交,不是搜索。
做事容易,但成功太難,除了靠客觀條件和個人努力等看得見的因素外,還有很多運氣成分。在硅谷成功的人,都承認自己只是比別人運氣好一點點。這倒不是他們謙虛,而是當他們回首自己成功的過程時,發現在很多需要命運女神垂青的時刻,他們都得到了庇佑。
在硅谷的歷史上,失敗和成功一直相伴,雖然大家關注的常常只是成功。扎克伯格經常在公司裏講「如果你沒有遇到失敗,說明你跑得還不快」,這既是對嘗試新東西的鼓勵,也是對失敗的寬容。
退出騰訊後,吳軍重返美國,開始了在常人看來極爲灑脫的生活方式。到全世界旅行,做風險投資,聽音樂會,寫暢銷書。
最耀眼也最奇怪的是,吳軍以毫不遮掩的精英主義,用類似記者的方式,從「Google 黑板報」到「硅谷來信」「吳軍的谷歌方法論」,不停歇地記錄了自己和家庭經歷的大事小事,瑣碎中卻將 21 世紀的經濟增長、技術變革、教育疑慮等大事一一記述了下來。
這樣一來,吳軍就從互聯網技術的領軍人物,蛻變成了互聯網生活的哲理導師。
 圖源:吳軍個人微博
圖源:吳軍個人微博
傳道,授業,解惑,從《見識》中用自己的人生經驗補充了讀者的社會視角,到《態度》中通過與兩個女兒的書信來往探討未來的努力,「被動地」成爲了吳軍生活中的一部分。
「姐姐上了好大學(MIT),是不是將來就會有好工作、好生活?」這是小女兒的問題。
「不是的,她以後還要努力一輩子。」吳軍答。
「既然以後可以努力一輩子,爲什麼要接受好的教育?不是有很多人退學創業成功了嗎?」小女兒又問。
30 歲的時候能實現財富自由嗎?職場中如何快速晉升?寒門如何出貴子?互聯網的下一波紅利什麼時候到來?……
今天,人們對於吳軍「來信」的期盼,幾乎到了飢渴的地步。其實,吳軍不過是抓住了作爲人類永恆的困境—夢想與現實的衝突這個關鍵。現在的問題是,浪潮已起,何時再及巔峯?
儘管吳軍認爲,「近一百年來,總有一些公司很幸運地、有意無意地站在技術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處在了那個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隨着波浪順順當當地向前漂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十幾年到幾十年間,它們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來臨。」
一生能趕上一次這樣的浪潮是幸運的。與別人不同的是,對於吳軍而言,他更快更早明白了一件事情,世事紛紜,無法預知下一件大事在哪個領域發作,爲了克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危機,必須立即反應,快速學習。
大衆的疑問和期盼,其實暴露了時代的弱點。但補救的方法不是大家共享一套成功經,也不在於能夠從互聯網中搜索到海量信息,而在於鞏固自己的力量。說到底,即使無數個吳軍都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分享出來,也不能證明在新一輪技術變遷的浪潮中我們就能佔領先機。
即使 2% 的人掌握了大數據和機器智能,也不代表我們沒有抓住智能時代的機遇,沒有認真對待挑戰的勇氣和可能。在吳軍看來,更重要的是,除了學習,你的思維框架還得有彈性、可包容、能擴展,還得有好幾套。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建議在現實中是如此蒼白無力。2017 年 10 月,吳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做有關通識教育、人文教育的報告。吳軍站在臺上,看到臺下坐的學生們居然帶了高等數學來聽報告。
「拿微積分怎麼找女朋友啊?我最後連這樣的話都說了。」吳軍無可奈何,又憂心忡忡。

見識 & 態度
講臺下的這片光景,是兩代人的代溝,也是每個人生的某種隱喻。
是的,孩子們的遊戲方式和規則變了。他們比吳軍更靈活地掌握應運而生的各類 APP,比吳軍更靈活地用技術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生活。但是,在後物慾和技術化的時代,如何應對那些變化、寬闊、龐雜、沒有規律、無視個人意志的現實,是做一個鎮定自若、着眼長遠的人,還是麻木不覺、投身佛系呢?
《黑客帝國》這部科幻味十足的電影中曾用多個鏡頭,重複了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人終將被緊緊捆綁在座位上,強迫觀看所謂現實的詭異影像。
「那個時候我覺得,改變大家的認知還是比較難的」,吳軍意識到。
當世界被處理在 Google 提供的龐大網頁裏,任何不能充分引起視覺刺激的文字、圖片或者視頻,都會被眼睛拋棄。而經過搜索引擎「搜索」後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地流動於眼前時,它對觀看者的思維與情感的摧毀力該是多麼強大,這樣的力量將怎樣重塑一個社會的頭腦與內心?
西奧多·羅斯扎克教授在《信息崇拜》中提醒:「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維的藝術。」從這個意義上講,吳軍的貢獻就在於「堅持寫寫書,豐富一下大家想問題的方式,或者說再開一扇窗子,看到外面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以至於在提及「機器智能取代人之後,人怎麼辦」時,吳軍會提到他喜歡的《紅樓夢》,談到《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吳軍認爲,人有兩個上帝賦予的特殊天賦是機器所無法取代的:一個是藝術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另一個是夢想和浪漫的情懷。而我們正在失去林黛玉那種「作詩的性格」。

談到這裏,吳軍是遺憾的,儘管這種遺憾已經被很多人重複過了。
信息論之父香農早在 1949 年就提出,信息是用來消除不確定的一種東西。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定義,卻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基礎。轉識成智,是不以知識本身爲目的的。我們抱怨的,不過是自己還沒有的那兩樣東西,我們放棄的,是沒有了雄心勃勃和靈性的社會。
面對不知疲倦地追趕信息技術的人們,吳軍總是會想起古希臘時代,那些在小劇場講大問題的「自由民」。
「記賬是技能,可以作爲謀生手段。但我們需要往上走一點,觀看錶演,欣賞音樂,讓生活更豐富。你不僅要履行分內義務,還要到廣場去辯論,出席城市事務討論會,爲國家的安全與繁榮擔負起責任。」吳軍說,「我們的目的是培養最大量的未來公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利益,覺得自己就是社會的主人。」
高效,不被打擾,是吳軍的態度。
與大多數人醒來就打開朋友圈刷存在感不同,「我看微信就像看郵件。每天只看兩三次,早上出門前看一眼,中午喫飯前看一眼,完了就幹其他的事。早上 1000 發的微信,不要指望我馬上看到。即使看到了,我也不會馬上回復,而是等會兒集中處理。」
「如果遠在美國的家人發消息找你呢?」
「找不着就找不着吧。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己的事自己解決。是生死問題麼?不是。沒有那麼多需要着急的事,你有更值得做的事。」
剛過 16:00,吳軍站起來走向房門,嘟噥道「第二個訪客應該已經到了」。他沒有看到助理髮送的微信,不知道第二個採訪計劃已經取消。
他是在提醒我採訪該結束了,雖然說話和聲細語、態度謙遜,也非常投入,但局面始終在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