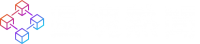從 2001 年 9 月 11 日至今已有 20 年,但對恐襲事件的目擊者而言,腦海中的深刻記憶依然沒有淡去——無論他們是在紐約親歷了這次災難,還是在電視上觀看了事態的發展。事件當天和緊隨其後的日子裏,現場的攝影師們拿起鏡頭、記錄歷史,捕捉到了體現人性、恐懼、絕望和希望的珍貴時刻。他們的作品自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意識,也永遠改變了攝影師自己。下文中,Artsy 採訪了五位攝影師——珍妮弗·阿特曼(Jennifer Altman)、斯坦·本田(Stan Honda)、喬爾·梅耶羅維茨(Joel Meyerowitz)、梅蘭妮·艾因齊格(Melanie Einzig)和古爾納拉·薩莫伊洛娃(Gulnara Samoilova)——五人娓娓道來自己的親身經歷,分享了他們在那不可磨滅的一刻記錄下的影像。


People flee the engulfed World Trade
Center Twin Towers prior to their collapse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anhattan, NY,
September 11, 2001. Rose Parascandola
is seen running after she escaped from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here she worked
© Jennifer S. Altman.
Courtesy of the
photographer
那天一大早,我爲了另一項攝影任務,正開車前往布魯克林。車行至富蘭克林·D. 羅斯福東河大道(FDR)上,我猛地擡頭一看——沒記錯的話,第一架飛機剛剛撞上世貿中心的雙子塔樓。大樓起火了。我就那樣把車停在了公路上,開始拿起鏡頭。一位警察過來招呼我駛離高速路。我立即去找任何可以停車的地方,一停好車便開始向雙子塔跑去。不知怎的,我打了個電話給我的編輯,說明計劃有變,我正在抓拍眼前的事情,不去布魯克林了。當我跑向世貿中心的時候,第二架飛機從我頭頂飛過。我跑到了近一些的地方,意識到必須更靠近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纔行,於是便動身前往富爾頓街(Fulton Street)和教堂街(Church)。
在我看來,最有衝擊力的畫面莫過於一位叫羅絲·帕拉斯坎多拉(Rose Parascandola)的女性——她穿着紅襯衫,尖叫着奔跑,身後是着火的世貿雙子塔。可以說,這張照片在一瞬間就象徵了一切。恐怖襲擊後,我有幸找到了她本人做後續的報道,還在作品最初拍攝的地方拍照留念。後來我又與她見了幾次面,知道她身心無恙後我很欣慰。在我看來,我們的生活永遠交織在了一起。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恐怖襲擊 10 週年的紀念日上。我們還是在原來的地方相遇,當時我正懷着孕,孩子九個月大。這次重逢讓我不禁感嘆,雖然二人的生活已經向前邁進了不少,但我們仍然是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些年接受的所有專業訓練都在那一刻達到了頂峯。我很清楚,當時的我正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說是一種使命。如今,我的攝影作品已經融入了我的身體。當我追憶那一天的時候,總是能夠清晰地看到那些圖像,看到那天發生的一切。當時的我正在捕捉人們最脆弱的一面;但與此同時,我也嘗試着告訴人們,他們並不孤單——社區圍繞着受傷的我們,每一個瞬間都充盈着愛與力量。
從那一天起——以及在這之前與之後——我都總是睜大眼睛完成任務。我明白,作爲一名攝影記者,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便是用人性、同情心與理解力去捕捉決定性的時刻。


Edward Fine covers his mouth as
he walks through the debris after
the collapse of one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s in New York,
September 11, 2001
Photo by Stan Honda/AFP.
Image via Getty Images
當時我在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工作,是一名合同攝影師。我想,對於那天的許多記者來說,事態比他們任何曾有過的災難經歷都要嚴重。當我走出地鐵時,兩座大樓都冒出了煙。那一刻,我還不知道有第二架飛機撞擊了大廈,因此感到十分困惑。當我走近世貿中心時,好像有成千上萬的人向我跑來,試圖逃離現場。在第一座塔樓倒塌後,一陣巨大的煙塵雲霧籠罩着整個區域。地面黑得如同夜晚,甚至視力都受到了影響。當時,我在一棟辦公樓附近,一名警察正把人們拉到大廳裏,讓他們脫離危險。見狀,我便順勢走了進去。不知何時,照片中的女性走了進來,身上沾滿了灰色的灰塵。她停頓了一下,我按下快門,一切就這麼成了。最後,我知道了她的身份——馬西·博德斯(Marcy Borders)。
當灰塵開始散去時,我又出門拍攝。氣氛可以說非常陰森。就像下了一場雪,所有東西都被灰色的塵埃所覆蓋——街道、建築、人、汽車,無一例外。人們穿過這些殘骸,離開事發地區。那大約就是我拍攝第二張照片的時刻,照片上身穿商務裝的男人叫埃德·費恩(Ed Fine)。在把照片發出去後我才意識到,從 78 層僥倖逃生的埃德依然拎着一隻公文包。人是故事的主角,因此我嘗試着把重點放在意欲逃生的人、緊急救援人員和相互幫助的普通人身上。
爲了展現發生的一切,我不得不尋求照片的幫助。對於很多攝影師說,通過取景器可以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身處混亂之中,我們的心思都在照片上。某種程度上來說,在世貿中心附近實地採訪的記者儘管身在現場,卻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而大部分的手機服務都已中斷。
我想,談論人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馬西后來已經去世,但艾德·費恩活了下來。最終,我們得以與親歷者見面,完成採訪與拍攝。能知道他們活了下來真的很棒。像其他攝影師和記者一樣,我只是在努力記錄歷史。


Joel Meyerowitz.The Plaza, 2001
Heritage Auctions
9 月 11 日,我在科德角(Cape Cod)出差。紐約徹底封城,以至於我五天都沒能回來。我真的很想回到紐約。作爲一個土生土長的紐約人,我想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幫助。在真的回到這座城市後,我便拿着徠卡走到了 9·11 事故的歸零地(Ground Zero)。人們豎起了圍欄,覆蓋了襲擊現場,因此你無法看到裏面的情況。當我舉起相機準備拍照時,一位女警察說:“老兄,這是犯罪現場,不能拍照。” 我回應道:“你在說什麼?這就是條街道。犯罪現場在那邊。” 她說:“不,朱利安尼市長說不允許拍照。”聽罷,我說:“真的嗎?這是美國當代歷史上最具歷史意義的時刻,他卻要禁止拍照?”
朱利安尼一直害怕人們會從悲劇中牟利。但身爲一名藝術家和歷史學家,這並不是我關心的問題:我只想在一切消失之前做好記錄。我當時大約說了“好吧,去你的,我就要進去,我要儘可能地拍”之類的話——製作視頻、拍攝照片,全力報道現場的情況。我搞到了一枚紐約公園局(Parks Department)的徽章,但警察還是會把我攆出現場。最後,我通過關係弄來了一枚貨真價實的紐約市警察局市長攝影師的徽章,花了足足幾個星期才辦下來。正是想爲這座城市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的衝動,才讓這次事件歷久彌新,而不是消失於歷史之中。我沒有記錄下所有發生的事情,僅憑一己之力怎麼可能做到呢?但我拍了 8500 張照片,將災難現場被拆毀時的重要進展存留在影像中。
我每天要工作 12 至 14 小時,攜帶 40 磅的設備,在災難現場周圍走上 10 至 12 英里,直到午夜後纔回到家中。這段經歷影響了我此後的工作與生活——從那以後,我開始更多地投身公共服務,而不是自己的工作。
在工地裏,地面在顫抖,煙霧徐徐上升。巨大的機器在不斷抓取、清除。噪音多到令人難以忍受,人們的清理救援行動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我站在那裏,雙膝發軟。我跪在地上哭了起來,目睹災難波及的範圍之大,體會兩百層樓房的轟然倒塌,是如此令人難以承受。這遠遠超出了我們個人在這座城市的定位與設想。對我來說,這些影像從未失去說服力,依舊讓人身臨其境。


Melanie Einzig, Church Street,
New York, September 11, 2001, 2001
© Melanie Einzig. Courtesy
of the photographer.
在 9·11 那天,我沒有跑到門外去拍照。就像照片中的送貨員一樣,我只是碰巧在現場而已。那天早晨,我正在中心大街上(Centre Street)做法院陪審員的工作。作爲一名街頭攝影師,我出門總是帶着相機,那天也不例外,我隨身帶了一個小的。當第二架飛機擊中世貿大廈時,我正在讀魯米(Rumi)的詩,等待法院呼叫我的名字。巨響傳來,乍一聽像是法院裏的炸彈爆炸,但我們很快就知道了那是什麼。官員們試圖將我們留在在法院裏,但我離開了,一路向西走,想看看發生了什麼。我一直是美聯社和其他新聞機構的自由撰稿人,但我當時並不迫切地想要把這些照片投餵給新聞系統。事實上,我等了八年才發佈這張照片。我逐漸意識到,我想做一種與衆不同的歷史記錄,一種更爲沉思、更加含蓄的記錄。那一天,你被懷疑、創傷和恐懼擊倒,很難理清頭緒。當第一座塔樓倒下時,我在腦海中隱約聽到了“你你你你…可以以以…拍張照片”的聲音。殘骸的塵雲湧上街道,人們都在四處逃竄。又拍了幾張照片後,我也驚恐地一路跑回東 12 街和第二大道的家。關於這張照片,人們有很多說法。其中最好的是呂克·桑特(Luc Sante)的解讀。

Melanie Einzig, Ground Zero,
New York, September 12, 2001,
2001
© Melanie Einzig. Courtesy
of the photographer
當我看到這些照片時,仍然感到異常悲慟、頭暈噁心。如今,我把照片獻給那些失去了親朋好友卻仍然堅強活着的人們;獻給所有努力尋找倖存者的消防員和工人;獻給我在“災坑”中遇到的那些在冬天還在清理現場的人;獻給所有身處附近和倖存下來的人——我們的喉嚨裏還卡着沒有喊出來的尖叫聲,也面對着其他形式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Photo by Gulnara Samoilova/AP
Courtesy of the photographer
9 月 11 日,我還在爲美聯社工作,住在離世界貿易中心四個街區的地方。因爲到中午纔去上班,所以事件發生時我還在家裏睡覺,直到不停的警報聲將我吵醒。電視播放着世貿中心其中一座塔樓着火的畫面。因爲我住的很近,所以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第二架飛機撞上南樓時,也在現實中聽到了聲響。我穿好衣服,把成卷的膠捲扔進我的相機包,跑到了世貿中心。
在拍照時,我通過取景器看到南塔開始倒塌。我設法按下了快門,立即聽到有人喊“快跑!”我跑上富爾頓街,摔了一跤,躲到了一輛汽車的後面。地面隆隆作響,汽車左右搖晃,一大團沉重而尖銳的建築碎片像颶風一樣襲來。一切變得非常昏暗。我看不見,也聽不見。我以爲我被生生活埋了。眼睛、鼻子和嘴裏都是灰塵,我開始使勁地喘氣。那一刻,我陷入了迷茫。我拿起相機,開始拍照。我是一個旁觀者,置身事外,看着事態的發展。攝影很多時候就是某種“肌肉記憶”,你要學會憑本能行事。可以說,我的相機拯救了我的理智:我的身體之所以能夠繼續運轉、保持專注,是因爲我基本處於“自動駕駛”的狀態。我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就有獲得世界新聞攝影大賽(World Press Photo)一等獎的那張。
我不記得有拍過這張照片,但不知怎的,我確實捕捉下了那個畫面。9·11 那天,我拍了大約 100 張照片(2.5 卷)。回到家,我開始在浴室裏沖洗膠片。不久後北塔倒塌了,灰塵湧進了我的公寓。
對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9·11 事件並沒有在那一天結束。20 年來,我們一直與之共存。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無法談論發生的事情,但通過繼續觀察、分享和談論我的工作和在那一天的經歷,我有了一種治癒的感覺。
Elyssa Goodman

相關文章回顧
**
**
!“9.11”20 年,5 位攝影師回顧當天的影像記錄!“9.11”20 年,5 位攝影師回顧當天的影像記錄